网上祭奠平台祭祀网祭英烈网上祈福祭扫公众号app平台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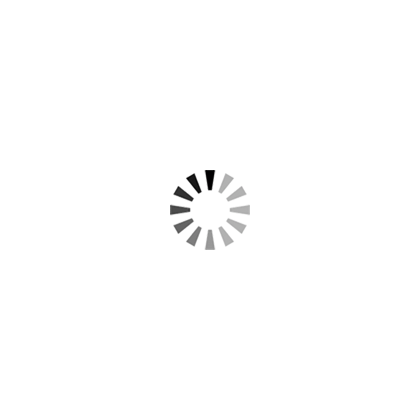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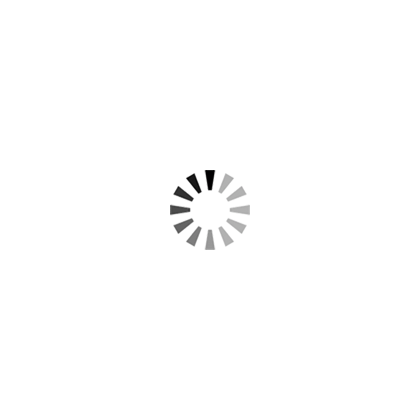
一、关注公众号 : jisijidian
二、点击公众号下方链接,进入页面——点击 “建馆”;
三、上传对应照片与简介:
四、点击祈福,选择祭品
五、邀请亲友共同追思,点击“祭拜着”,点击“+”,分享链接给自己的亲友。
文学批评:偏至还是掘进?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史》说起
王冰
王晓明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是当代文学批评史重要的著作,此书分上下两卷,分五辑,收录了22篇文章,其间的论文讨论了二十世纪以来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重新分析了众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全书所选各文章多显示了与传统的文学史观较为不同的理论趋向,对一向被视为非主流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如被压抑的现代性,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述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等等问题,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深入研究。全书持论新颖,富于创造性,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最新和最为持重的研究成果。
可他选编的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在探求的过程中过于追求一种历史的细节,在力图寻找到别人没有触及的新的领域和视角时,表现出他们在探讨问题的偏至性和执拗性。
比如在王德威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就将自己的思维一头栽进晚清小说的念头里去。认定晚清小说与传统小说有剪不断的脐带关系。可他忽略了一种重要的东西,就是学者们早就告诉我们的,在作家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叙事方法、主题关怀、以及意象运用以前,中国现代小说是无由兴起的。其实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自己预设的观点而故意弃之一边罢了。我不是不同意晚清小说并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而是如果将全部的因素都往这个方向上走,这种研究就变得执拗,甚至是危险了。由此重审王对“晚清文学”的时间界定,他的“现代性”想象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这段时期的晚清文学“现代主义”化了。
而林基成在写作《重读《天演论》时,却将自己的笔力集中到了很边缘的表述中去,而忽略了主要的意旨,也出现了一种偏至 ,他认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译者未加说明的增译部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译者对原作的改动。”“从中看出,‘天演’首先是对‘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对‘能够持续下来的’内容及‘不变者’的解释——的直译。问题在于,译者有时又以‘天行’来译‘Cosmic process’,他的翻译手稿在这段译文中亦没有用‘天演’这词;这是否意味着用‘天演’来译‘Cosmicprocess’只是他修改手稿时的偶然借用?”“和赫胥黎原作比较,严复在《天演论》中比较重要的漏译首先是关于宇宙进程和进化的关系,至少有二点重要的遗漏”“他还指出,“进化不是对宇宙过程的解释,而仅仅是对该过程的方法和结果的论述。”这些都是很具人工化的斧凿的推测,主观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其实,作为文学批评,它常常要求理论家从一定的文学理论出发,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的评价,以便指导当前的文学写作。这必然要求一个评论家学术视野开阔广博,思想立论谨慎严密,并能通过梳理分析众多的作家作品,开启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的文学视角,为当代创作的批评和写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它要求善于发现覆盖在一种现象上的某种本质的道理,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作家理论,作品理论及读者理论展开比较系统的梳理,以比较开阔的文化为背景,力求在理论的层面上,来寻求客观存在着的内在规律。作为全国卓有影响的评论家,王晓明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史》是无疑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对于文学理论的把握的精到和熟稔,以及他对当前文学评论整体性的理解,使他在文学评论的编选走在了这一领域的前沿位置,从中我们能明显见出他对文学理论进行总结归纳的综合性的特点,这点是具有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质的。他选编的这些理论并非机械简单的,而是通过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挣脱传统理论的约束,以更为公允、辩证的眼光认识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写作和评论的各种现象,并在其中提出了许多充满辩证思想、可资后人借鉴的艺术创作经验。可以说,王晓明在选编过程是渗透着他理智的思辨的,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指导性,它有它的体系性,并且充满着人文精神。他的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拓展了传统文论的研究领域。他的理论倾向于文学自身的内在、本体,以及从本体论视角对纵向历时性发展规律和横向共时性特点进行审视和阐述,并以崭新的风格、独到的指向,探索了某些新的审美观、批评观,因此他的理论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超前意识,有其理论前置性、预见性、指导性和超越性,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批评和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可他编选的前提依旧是有问题的,因为一般说来,文学批评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一切文学现象的分析和评论。它是一门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要求有一定的系统和理论深度。即文学批评要实现文学写作与文学评论连通的中间环节,起到了一种推动文学创作的作用,可王晓明选编的理论文章,其内容更多关注的是文艺的具体操作方式,注重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写作的具体功能和作用,并表现出极大的偏至性和执拗性,他编选的这些论文具有共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史料钩沉的偏至,立论出发点的偏至,论证的偏至,结论的偏至等等,其实质是危险的。
他的这种偏至体现出文学批评界一种共同的倾向,同时也是一种焦躁的表现,也体现出一种批评资源的匮乏,就如同王光明等《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中讨论的那样,“文学批评失去了传统的归顺或反抗对象之后,似乎一直在无人之阵中左冲右突,在无人之阵中自我面对,从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的兴起与试验,‘学院派批评’的提出,到如今文化批评的普遍盛行,文学批评始终在调整和寻找更有效的切入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这些加油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仅带给批评新的视野和境界,也使批评变得更加多样与丰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批评的缺席’到今年前几期的《文论报》头版头条以非常醒目的标题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惊世骇俗的姿态我们当然不必认同,可文学批评的左冲右突和现实问题却需要正视,我想这里恐怕确实存在东风他们所说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的问题,我们的批评在回应90年代的文学现实时,显得还不够有效,不够有力,未能赢得人们包括批评界本身的同情和认同。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症结在哪里?怎么样去建构更自觉、更有效的批评?”(王光明等《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山花》2000,10)而当景况进一步发展,甚至到了黄子平先生所说过的“创新之狗追得人连站着撒尿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大多数批评家,则是将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直接搬进自己的文本之中,而却是生吞活剥的套用,而不是根据文本进行解读,更多的是预设一个前提,然后用相关的理论加以归类,寻找材料,得出一种必然的结论,因此相当的批评没有激情,文字晦涩干瘪,成为纯“象牙塔”中的东西,不注意关注新作家新事物,新现象,只是在一堆故纸堆里绕来绕去,刻意地去寻找新意,而这种新意却又是相当牵强的,于是相当一部分批评家在给一流的创作做出三流的文学批评;给三流的创作做出一流的文学批评。特别是过度的理性使所谓一些学院派的批评家,把韦勤克、佛克马、杰姆逊、福柯、拉康、德里达的理论奉为圭臬,而不能很好的加以辨别,这样就使文学批评成为创造一种新理性的手段,而不是阅读文本的工具,最后文学批评向一种所谓的理论投降了。其中的弊病是它更多讲究学理背景、学术积累、知识传统、学术规范等,而放弃了在这背后有一种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确立的诉求,即在设立“他者”的时候并没有同时确立自我。所以我觉得能像胡河清一样,能将各种知识背静融合在一起,深入到文本的批评家是越来越少了,因此文学评论表现出更大的一种偏至性。
记得杨扬在《论90年代文学批评》谈到“由几个所谓的思想人物圈定一二个问题,然后大家围绕这一二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思想生长方式,大概只有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思想年代才存在。”(《南方文坛》200005),当这种局面结束之后,更多的批评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角度,以至成为一种偏至,而不管这种角度是否合理。也就是说,90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脱离了那种主潮式的生长方式,而分裂出多种多样的话题,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和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谓的多样性,是就文学批评具有多样发展的精神空间而言的。可其方向上的合理性还有待讨论,我认为文学批评的主要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不断为我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感受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精神动力,而在于这种前瞻性的思想是否能够通过批评家不断与当代艺术的对话中,体现一种研究方向的敏锐性。而从文学史的进程来看,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都具有一种超凡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直接体现为批评家在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敏感,能够不为既定的价值观念所淤,排除陈见,提炼出那些不为时人所看重,或不为时人所注意的新的思想萌芽及审美胚胎。
可这点在当下无疑是缺乏的。
虽然近几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质量还是相当高的,颇具学术含量,展示了文学批评的成果,凸现出文学批评力量的壮大,比如陈思和、王晓明策划主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包亚明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世纪风丛书”,陈思和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谢冕、孟繁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文学总系”,以及杨匡汉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可更多的批评家们都急于创新,急于在人面前展示自己所谓的新发现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趋势,于是一些声调高亢,底气似乎很足的批评一下就涌现了出来,似乎一下能够夺人眼力了,可事实上的非批评的因素却是昭然若揭,比如对余秋雨现象的批判,比如《十作家批判书》这枚重磅炮弹的抛出,比如《芙蓉》在刊出的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等等,按编者的话说就是,“观点如此之偏激,其文风如此‘不规矩’,势必招致强烈反对”。因此学术问题的艰难积淀、批评理论和方法运用的渐趋成熟、健康的批评格局的逐步形成等方面仍旧需要我们的加油。
其实这种偏至不仅仅是非主潮式的问题,更是批评家的一种心态问题,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的不同,它不再单纯关注于对纯粹的文学文本的探入,而更倾力于进行文本背后的挖掘,这种加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可关键还是一个度的问题,那么他们是在做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呢?单就这点,就很令人担心。因为文学批评不单是个人艺术趣味问题,它需要承担文学史的责任,需要对新一代的批评家们负责。也就是说他不能淹没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去开掘一些琐碎的东西。
而这种偏至也似乎将要成为一种潮流,呈现出地域分布的特色。90年代,批评界一度流行这样的说法,就是“后北京”、“新南京”和“旧上海”,这种概括虽然有待商榷,可都涉及到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且文学批评中的语言也渐渐分化并且怪异晦涩,并且九十年代文学的消费主义倾向在文学批评界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过剩和文化符码的不断复制。有人说“90 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呈现瓦解状态”并非危言耸听,丁帆在《批评癔病的初诊》(《文艺报》1997年6月7日)批评文学批评家们得了“癔病”,“真正的批评家缺席”、“失语”。这点我是认同的。于是作家感到了困扰,批评家也陷入了困惑。为了对抗这种商品大潮,更好地推销自己的精神产品,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再次合谋,不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先是有王一川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茅盾被除名,金庸等人取而代之。到了1997年,则有所谓“马桥之争”,接下来就是就对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否“抄袭”《哈扎尔词典》的讨论,还有90年代对谢冕等人主编的两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争论;以及攻击余光中是“文学上的大反攻,反攻大陆”的风波(《华夏诗报》 1993年第5期所刊一位中学生的来信。)等等,都反映了作家的一种偏至和焦躁。
古远清先生在《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谈到,“可评论家们爱走极端。当他们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建设的时候,又有人效仿思想家去做宏观的文化批评。这种批评如写得好,的确能给人高屋建瓴之感,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文化批评显得大而空,这种批评的一大特征是爱用大词,诸如‘全球性’之类。这种‘全球性’的滥用,使80年代风行过的细读文本的新批评相形见绌。” (古远清《学术研究》200005)就很恰当地指出了这种不良的倾向和势头。景秀明在《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几种不良倾向》(《文论报》200102)中也批评说:“文学批评的泡沫化。如果说文学批评的传媒化是由于个人表现和商业炒作的动机与目的造成的,那么文学批评的泡沫化则相当程度是由不合理的文化机制产生的结果。近年来的文坛,不是缺少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是缺少一种具有深度和原创性的文学批评。这种具有深度和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是具有范式意义的,它是一个时代或一段时期,文学批评的水平与成就的最集中体现。具有深度和原创性的文学批评的匮乏,已经引起了批评界的高度重视。在近年来的文化批评类的报刊上,充斥着大量无学术观点,缺乏深度,乃至重复写作的泡沫论文。”这种状况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已有文学批评的虚弱、无力与盲目。我认为,提高批评家的责任问题是解决的途径的一个方面,即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批评家们为后来的人们创造积淀了什么,这成为了其中的关键。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更从容、更审慎、更辩证地来对待各种资源,而避免以往那种急功近利和简单片面,从而将自己的研究,放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加以读解阐释,阐扬其内在价值,激活其理论生命,在阐释中生成具有真正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话语系统。
于是面对他的厚厚的两大本《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史》我不禁要问,他选择的论文是偏至还是掘进?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维还是一种死胡同?是代表了研究的新方向还是一种研究的末路?是一种代表了一种资源的穷尽,还是引领文学批评走向了一片新领域?那么我们不禁再一次的担心和发问,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最终将要走向何方?
代操办 加微信看看!
师父微信: wangzijin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