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祭奠平台祭祀网祭英烈网上祈福祭扫公众号app平台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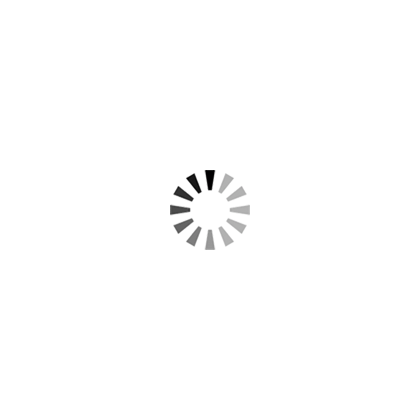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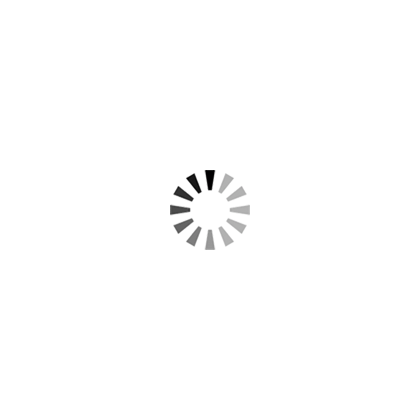
一、关注公众号 : jisijidian
二、点击公众号下方链接,进入页面——点击 “建馆”;
三、上传对应照片与简介:
四、点击祈福,选择祭品
五、邀请亲友共同追思,点击“祭拜着”,点击“+”,分享链接给自己的亲友。
我30岁生日那天,父亲来电话,说爷爷去世了祭爷爷。我握着话筒就哭了,如同爷爷身边的那个10岁的、16岁的女孩子一样地哭了。爷爷怎么可能就去世了?去年12月我还见过他,他的皱纹还舒展着,眼里满是暖暖的笑,他只是脚有些肿,走得慢了点,他只是抚摩着我埋在他怀里的头,说:爷爷这次没法送你去车站了。爷爷的怀抱是确确实实温暖的,难道我从此不能将头埋入其中了?难道我再不能摩挲他灰白而稀疏的胡子,再不能悄悄地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真的,爷爷怎么能像风一样的没了?找寻不着了?或者爷爷化做了其他形态,只是我不知道吧?
也是这样的夏天,这样的傍晚,太阳已经落了山,地上还散发着余热祭爷爷。爷爷端来水泼洒我家临街的青石板地面。天边有红色的晚霞,渐渐颜色越深越沉了。爷爷搬了个竹躺椅,临街躺着,我搬个小凳子,坐在他的膝边,将头枕着爷爷的腿,爷爷轻摇扇子,也赶蚊子,也为我扇凉。门前有两棵柳树,那是爷爷种的,有10年了,风过去,枝叶婆娑,柳叶儿不时地飘落在爷爷的肚皮上,我的发梢末。爷爷问我:“阿红,爷爷死了,你扛脚还是扛头?”10岁的我并不很明白“死”,想了想,说:“我扛头。”爷爷笑了,继续逗我怎样扛头呀之类的。
这是一条繁忙热闹的小街,青石板的路面被午后的雨水冲刷得溜光祭爷爷。有踢着拖鞋嘟着嘴一路小跑过的小男孩,有卖豆腐的晃悠晃悠挑着担吆喝他的最后一块豆腐,邻家阿婆瘪着嘴咀嚼着什么向爷爷抱怨青菜又贵了,那穿花衬衫留长头发的小伙子拎一个四喇叭收音机吹着口哨抖着脚,而姑娘的高跟鞋清脆地从街那头响起,一路地绵延到这头。我的婶婶那时还在和叔叔谈恋爱,很多的傍晚,她从另一条小巷穿过到我家门前,看到爷爷躺着,总是很羞涩地问了安,站在街对面,抬头朝我们家的二楼窗户喊:阿灿——,我的叔叔就乒乒乓乓冲下来,爷爷朝他们笑,叔叔朝我扮鬼脸,姑娘的脸被最后的一丝霞光映红了。那时的婶婶穿一件小圆领的绿色衬衣,白色的百折裙,有两条齐腰的长辫子,辫子上扎了绿色的缎带。
他们走了,我的故事会就开始了祭爷爷。爷爷会问我,莆田名字怎么来呀?看我摇头,爷爷便满眼得意,说,莆田原来是海呀,海水退了,变田了,到处长着蒲草呢。又说,莆田还称作荔城,因为到处是红红的荔枝呢;有一年,黄巢军一路南下,来到莆田宋家,那宋家有一株千年荔枝树,他在树上砍了一刀,以后这株荔枝树结的果子壳上都凹进去一圈,人们引以为奇,争相购买,荔城之名就传开了。爷爷还告诉我,莆田出了不少名人呢,书法家蔡襄,诗人刘克庄啊,都是。宋朝的皇帝曾赐给莆田一个名儿——文献名邦,以表彰莆田读书风气盛,据说有一年科举考试,居然有49名举人是莆田人,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就抚摩我的小脑袋说:“我们阿红也会是举人呢。”于是,爷爷总不免要说起莆田的两个奇女子:一个就是建成木兰陂,拦河蓄水、灌溉兴化平原的木兰女。据说几次修堤皆因水流湍急失败,木兰女以身投水,感动上苍,风止水停,终于成功,而木兰女的尸体随水漂流,几日夜不曾变形,人们说她早已升天,河面上漂流的不过是她的躯壳。另一个奇女子就是后世名震沿海的妈祖娘娘,她原名林默,是莆田湄洲岛的一个少女,每当海边风急涛涌,她的魂灵就守护在海上,救护遇难的渔民,后来她在一块巨石上升了天,岛上的居民都看见神仙来接她,据说,郑和下西洋,清军收复台湾,都得到过妈祖的帮助呢。
在我年少的时光里,爷爷展现给我的是怎样的丰富绚丽的世界:倭寇侵扰沿海呀,戚家军带的“光饼”呀,隋炀帝看琼花呀,乾隆爷游江南呀,莆田的19日夜的大火,日本飞机来的时候躲在观音的庙里,抓壮丁,练钢铁……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演义,在爷爷的嘴里全成了故事,全成了我瞪大眼睛,张开小嘴,凝神看待的世界祭爷爷。我搂着爷爷的脖子问:“爷爷,你怎么懂这么多呀,我怎么不知道呢?”爷爷会摸摸他圆鼓鼓的肚子说:“爷爷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在这样的一个个夏天的夜晚,爷爷教会我去热爱知识,去用好奇的心体察世界,而我后来之所以那样喜欢讲故事、听故事,全出于爷爷给予我的每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
有时候,爷爷喜欢在露台乘凉祭爷爷。尤其是夜来香开了的时节。我家是老式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厨房、客厅,爷爷奶奶的卧室;楼上是叔叔和我的卧室,以及露台。露台铺着红色的方砖,一面有木质的围栏,小的时候,我一爬上露台靠近围栏的凳子,爷爷就惶惶将我拽下,掉到楼下不是玩的;一面是堵泥墙,泥墙只有爷爷的半身高,我长大了,可以望见隔壁家楼上姑娘的房间,有圆的镜子,粉红的被,有时那姑娘探身伸手关了木窗户,我便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听到有断续婉转的歌声。露台的正面也是半身高的泥墙,隔壁家的一株龙眼树,将茂盛的枝桠伸进来。三、四月时候,白色细小的龙眼花开了,爷爷眯缝着眼睛说:“今年龙眼要丰收了。”有时候,爷爷会冲隔壁伯伯叫:“花太密了,打掉些,要不果子长不大。”
爷爷是拿种花的知识对待果树的祭爷爷。七八见方的露台上摆满了爷爷的花。月季花最多,红色白色的,一开,满眼姹紫嫣红,台风过后,满地花瓣儿,爷爷便和我将花瓣儿扫了,倒在花盆中,说来于泥土归于泥土;后来我看《红楼梦》,林妹妹也说泥土是最洁净的,将花埋在土里比随水流去还洁净。每日爷爷都一一清点他的花:金桔累累挂满枝,石榴花红红的笑,海棠花这边谢了那边开;那株百合花,只长长的一根茎,已开了12朵花儿;紫色的丁香花忧郁地在墙边开着。那株种在花坛里的茉莉花是爷爷最欢喜的了,它总在晚上结花苞,喝了一夜露水,次日一早就哗哗哗开满了,一两百朵,洁白的散发着浓郁的香。在那样透明的早晨,爷爷提个竹编小篮,低头弯腰摘下茉莉,放入篮中。我在睡梦中醒来,一缕幽香沁入心间,只见枕边有几朵白花儿静静呆着,花瓣舒展,带着露珠儿。爷爷提着花篮下了楼梯,将花倒在桌上,细细挑出几朵大小一般的茉莉,齐齐地一朵朵插在木梳上,再将木梳斜插在奶奶的发髻边,爷爷说,奶奶年轻时候,头发黑亮黑亮,长长的,盘成髻,插茉莉花最好看了。后来我在街上看到老太太头上的茉莉,便总想到每个那样的清晨,奶奶坐着,爷爷站着,手上是插满茉莉的木梳。多下的茉莉花自然将它们晒干了,加在绿茶里,那味儿没说的。普鲁斯特在吃一种小饼的时候,回到了在贡布雷的时光里。如今我喝过许多次花茶,却总找不回爷爷调制的味儿。现在我在庭院也栽了一株茉莉花,每次会开十来朵,我总将它们收在一个瓷瓶里,枯了也不烂,就那样干着,散发着淡淡的香。爷爷说,花儿都是有生命的,花儿知道人疼它,就长得好。
在那样的夜晚,风儿吹过,忽隐忽现的香味飘来,爷爷闭上眼睛,摇着扇子,说:“这是夜来香的香味,这下又是兰花的香了祭爷爷。”白话小说中有一则叫“灌园叟晚逢仙女”,讲花痴秋先种得满园好花,却被恶霸打个粉碎,有牡丹仙子下来人间,将花复活,惩治了恶霸,花翁也跟着成仙了。《聊斋》里也讲花神为报答爱花人,化做美丽的女子相伴。也不知道哪本书说的,一个爱花的人,他总不会坏到哪里去的。那花儿多么美好,天天对着她,怎么会生出龌龊的心思呢?爷爷如此的爱花,想他的魂灵定是在与花仙相伴了。
“灌园叟晚逢仙女”的故事最初是爷爷告诉我的祭爷爷。爷爷肚子里的故事多半从戏曲中获得。在莆田流行的是莆仙戏,用莆仙方言演唱。莆仙戏源远流长,宋时名“优戏”,将宋杂剧混合“吴歌”、“楚谣”以及当地民间歌舞而成,至明代融合弋阳诸腔,产生地方特色的“兴化腔”,被称为“兴化戏”,直到建国后才称为莆仙戏。和很多地方一样,有一个村社的社戏,也有到城里搭戏棚庆祝节日的,自然也有正规的戏剧团。爷爷对官办剧团的生、旦诸名角也并不都以为然,有时会和票友门说:“还是秋塘那个戏班的青衣嗓音亮,扮相也好。”
逢年过节,或是菩萨生日祭日,会有很多社戏,爷爷和票友们便也三五成群出城观剧祭爷爷。就如三月姑娘踏春一般,仔细收拾了才出门:一身黑色的湖绸夏装,一把折扇,一双黑色布鞋,头发梳得溜光,从小巷出去,一路回头,看自己衣服哪有褶皱呀,哪有小棉絮呀,就这样摇摇摆摆的晃到小巷口。这是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呢。曾外祖母和奶奶都这么描述的。说爷爷的爷爷是县爷,在曾祖父时家道就没落了,可是爷爷还是带点纨绔子弟的样子,奶奶嫁他之前,曾偷偷地去看,那时候爷爷开着一片店,打烊了,门扇却半开着,爷爷坐在柜台前,拉着二胡,旁若无人。我看到的爷爷,中山装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折扇还是带的,一双旧的大头皮鞋不很黑亮,但没有一点灰尘。
爷爷和票友们去看戏,一看一天,奶奶就唠叨,也许是习惯了,那唠叨听来更像是例行公事,不过爷爷要是陪曾外祖母去,奶奶就不吱声了祭爷爷。可有一次爷爷和曾外祖母过了午夜还没回来,奶奶已经哭出声了,叔叔们都分头到熟悉的票友家去探听。夜里二点,却见爷爷搀着曾外祖母,曾外祖母拄着拐杖,从街的黑暗处走来,一个半白的头,一个全白的发髻,街灯将两条影子一会拉长一会变短,爷爷似乎还和曾外祖母在争辩什么,声音远远地荡在小街夜的深处。面对奶奶红肿的眼睛,我们满脸的焦虑,爷爷傻笑着,曾外祖母中气倒很足:“哭什么?没死呀,我们到七街去看戏,回来走错路了。”我们偷偷觑着奶奶的神色,知道爷爷今天晚上要倒霉了,都四散睡觉去了。后来就听见奶奶半哭半数落的,没爷爷的声音,爷爷的声音开始的时候,讲的是当晚上看的戏文故事。爷爷嘴巴在讲着,那思维已然停顿了,还伴随着微微的鼾声,中间夹着奶奶的不满:“‘庵堂认母’是《玉堂春》里的,怎么《望江亭》也有这一段?喂,喂——这死老头子……”
在这样的夜晚,爷爷总是将许多故事换了包,奶奶听多了,是能指出谬误的,有时候呢,也被混了过去祭爷爷。也难怪爷爷呀,中国戏曲故事很多都一样的呢,总有这样的郎才女貌,最后都中了状元,合家团圆的。爷爷不那么困的时候一出出故事是不会串调的。爷爷有一本“帐册”,发黄的牛皮纸订成的厚厚的一叠,白色封面上有爷爷用毛笔写的二个字:“戏文”,翻开了,其中记着:某年某日某地,看某戏,小旦某,小生某。不看戏的时间里,爷爷常将“帐册”翻开,用他在私塾读唐诗的声音读那些戏文的名称,全是对偶的句子,串将起来读,抑扬顿挫的。有时,爷爷也会轻轻地哼着某段,一手摇着扇子,微闭着眼睛,一手在腿上打着拍子。这时候,我悄悄的将剥好的桂圆塞到爷爷嘴里,爷爷吃了一惊,睁开眼睛,用扇子打一下我的屁股,我便缠着爷爷讲《百花亭》的故事。
不看戏的时间里,爷爷会带把二胡到田尾的王家爷爷那里去,几个老头组成个“十音八乐”祭爷爷。这“十音八乐”是莆仙一带特别的民乐合奏,乐声婉转协和。爷爷在那个小团体里任二胡,有时候也客串笛管(也叫芦笛),这笛管是种古乐器,类似古筚篥,用黑色的尚书木制成,头大尾小,形似喇叭。其他的乐器,打击乐有各种的鼓、锣和钹,管弦乐器除笛管外还有梅花(也叫大吹,类似唢呐)、横笛、大胡、二胡、尺胡、四胡、八角琴、月琴、三弦等。爷爷说他不会看五线谱和简谱,他们学的是工尺谱,连同指法都是代代相传的。平日他们聚在一起温习,到了节日,会有街道居委会给搭个台子,他们几个老头就在台子上,吹奏那些惯熟的曲目。可惜我那时候我还小,对这些曲目一点不感兴趣,便从来不听的。只是有一年年初一夜晚,我到同学家去,穿过一条青石板的小巷子,远处有人放鞭炮,小巷静静地延伸着,只有两户人家门口亮着红灯笼。突然,在小巷深处悠悠传来音乐声,是“十音八乐”的旋律,如流水,如青丝,缠绵地,持续地述说什么,在那样的夜晚,似有若无,空气中便有了温暖而感伤的味道。我不知道这个“十音八乐”组合是否就有爷爷在,那时候我还小,第二天也就忘了问。现在想问,也问不到了。
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去了一趟眉洲岛妈祖庙,刚好碰上祭妈祖的社戏,戏台前密密地站着许多当地人祭爷爷。我也站着听锣鼓热闹地响,演的是《白蛇传》。爷爷曾经牵着我的手去看过的。离戏台不远的一个木房子里有几个老人坐着喝功夫茶,几件乐器散放在桌上椅上,那些乐器全都陈旧地斑驳着,我想上前摸摸,有个老人,脸皱成核桃样,眼里却有天真的笑意,他说,我们是演“十音八乐”的,他拿起一件“梅花”,随意地吹了一下,一个清亮高亢的音符蹦出来,他脸上的笑意更重了。哦,亲爱的爷爷,假若我能再见你,能教我一曲么。
莆田的街道拓宽了,青石板的小巷子越来越少;我家那临街的楼房拆了,奶奶叔叔搬到了7层的套房里祭爷爷。阳台没了,种在泥坛中的茉莉和昙花搬不走也只能丢弃了。新房子的一间挂着爷爷50岁时的放大照片,头发还是黑的,穿一件中山装,额头发亮,嘴角略略上翘,从怎样的角度,他都在看着你。爷爷的房间放着从老房子搬来的那架竹制双人床,依旧挂着蓝布蚊帐,似乎主人昨天还在。爷爷重病卧床的时候不让父亲告诉我,我知道,爷爷不希望我哀伤。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 对于生的爷爷我无法穷尽他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对于“死”,我只有一次体会,那是我14岁时曾祖母的去世:她睡在竹床上,微微蜷曲着身子,阳光从屋顶的一块明瓦透进来,落在她的身上,那身子那样单薄,像一片枯叶,安静的呆着。是的,爷爷只是睡着了,或者,爷爷只是转化成另一种形态,他一定在那样的世界中,知道我在想念他,他一定会知道我也喜欢种花,喜欢说故事,于人于事也一样乐观对待。
代操办 加微信看看!
师父微信: wangzijinci